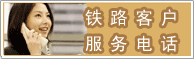今年是广州火车站新站建站40周年。我采访了列车员、客运员、售票员、乘客、机工等超过20人,记下了超过50页的采访笔记。有一家三代都在火车站工作的铁路子弟,有刚刚成为列车员的90后小姑娘。她们,连同火车站近万名员工一起,见证了40年火车站走过的岁月沧桑。 1972年,17岁的梁少英成为了一名票务员,负责广州火车站检票及进站的工作。那时,广州火车站还是位于大沙头的广九旧站,她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了超过30年。 解放前,梁少英的父亲是一名司炉。在蒸汽机车时代,司炉负责给蒸汽机车铲煤、润油,以控制蒸汽压力。梁少英的父亲最远随车跑到了武汉,那个时候从广州到武汉,需要两天两夜。解放前跑一段广州到武汉的旅程,在当时算得上是“威水”史。在铁路子弟中,梁少英常常因此而自豪。 这段超过1000公里的路程,如今只需要4个小时的高铁就能到达。 梁少英工作两年后,大沙头火车站被弃用,位于流花路的广州火车站投入使用。大沙头火车站停用时,每天只有5趟发往武汉、北京、长沙、西安、郑州的长途列车。新站启用后,现在仅属于广州客运段的普通列车就有16.5趟。 铁路一点一点变化。民国时期,分为一等座、二等座、三等座的车厢,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硬座、硬卧、软卧代替。原本只能用来运输军队的棚车,因为没有了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后用于运载短途或春运乘客。但无论如何,进步是明显的,从黑色的“闷罐车”,到绿色非空调车,红色空调车,蓝色特快,再到白色高铁。 梁少英的父亲在退休后不久,司炉这个职位也消失了。蒸汽机车在上世纪80年代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电气机车成为主流。梁少英记忆中那个坐火车时煤灰随风飘进火车头后两节车厢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 一同消失的还有硬卡票,那种全国通行了近50年,长方形硬纸板制成的车票,已经被一张薄薄的带有二维码编号的新型车票取代。 提起几十年来的变迁,多数上了年纪的铁路子弟都感慨万千。他们时不时会流露出对那个年代的些许怀念。梁少英跟一名铁路子弟结了婚,因为广铁集团被看作“铁饭碗”,他们门当户对,但她没有让女儿进入铁路系统工作,因为待遇与前途都大不如前。 现在,新进入铁路系统的员工们,更愿意去南站,为白色的高铁服务。那里没有泡面、鸡爪、瓜子、香烟和厕所的味道。 南都记者 杨希越 作者:杨希越 |
火车的黑白变迁(图)
时间:2014-04-28 12:24来源:南方都市报
通途网提醒:以上内容来自新闻媒体,仅供参考。
------分隔线----------------------------
- 上一篇:与铁路青年对话爱情
- 下一篇:新西兰奥克兰城市铁路电气化 下周一新车正式上路